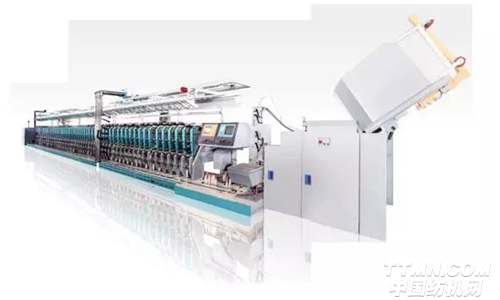黃道婆:三十多年崖州學藝 終成一代“紡織女神”
眾所周知,黃道婆是我國偉大的棉紡織技術革新家。然而,鮮有人知的是,黃道婆少時淪落三亞,在崖州學藝生活了30多年,向當地百姓學習紡織技藝,并帶回松江烏泥涇,然后通過自己的努力,革新了棉紡工具和棉紡技術,不但促進松江烏泥涇棉紡織業的發展,而且迅速傳播到江淮、湖湘、川蜀乃至中原地區,對十三世紀中國紡織業的發展做出了不朽的貢獻,從一名卑微民女變成名揚天下的“紡織女神”。
黃道婆是哪里人?一說上海烏泥涇人,另一說崖州人
“黃道婆是哪里人,為何會淪落崖州?”海南熱帶海洋學院教授林日舉回答采風團讀者,黃道婆出身微賤,史書沒有給她立傳,由于她為松江烏泥涇人作出貢獻,逝世后鄉里人為她立祠,關于她的故事就在民間開始流傳。
最早記載黃道婆事跡的文人著述當屬陶宗儀的《南村輟耕錄》和王逢的《梧溪集》,這兩本書中都提及黃道婆。其中,《南村輟耕錄》里寫道“有一嫗名黃道婆者,自崖州來,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……”沒有明確說黃道婆是哪里人。而后來的《梧溪集》記述:“黃道婆,松之烏泥涇人,少淪落崖州。”對黃道婆的生平和籍貫做了補充。
林日舉認為,陶宗儀移居松江府寫作《南村輟耕錄》的時間,距離黃道婆回到烏泥涇的年代不過五六十年,黃道婆在松江地區的影響還在延續,所記事跡應是可信的。而王逢在烏泥涇生活了20年之久,寫作《梧溪集》時距黃道婆回松江時也不過60年,且《梧溪集》是應上海知縣之邀而作,作時必經一番深入了解,所記黃道婆事跡應是屬實的。
由此可以得知,黃道婆是松江府烏泥涇人,少年流落到崖州。“這兩本書關于黃道婆的記述很簡短,到新中國成立后,人們不斷地挖掘地方志、傳說亦或是民族學的材料,這個人物才逐漸豐滿起來。”林日舉邊說著邊從背包里掏出一摞有關黃道婆研究的書籍、論文來。
資料顯示:據調查,黃道婆出生在松江烏泥涇的一個貧苦勞動人民家里(出生的年代大約在南宋理宗嘉熙末或淳祐初年,約1245年)。幼年當童養媳,由于受盡封建禮教的虐待,黃道婆實在忍無可忍,毅然在一天夜里逃了出來,匆忙間躲入停泊在黃浦江邊的一只海船上。原來這艘海船是要到崖州經商的,她就這樣隨著海船離開了故鄉,到了海南島的崖州。
“關于黃道婆的身世,研究界還有一些別的聲音。有些研究者認為黃道婆就是崖州本地人。”三亞市作協原主席、市政協社法委原主任羅燈光則認為,陶宗儀和王逢對于黃道婆的記述過于簡短,且不夠詳實,尤其是王逢的《梧溪集》寫黃道婆的內容是詩歌創作,可信度較低,關于黃道婆的籍貫歷來有爭論,這兩本書籍中都沒有寫清楚,且年代久遠,缺乏有力史料佐證。
“我與諸多本土文化人認為黃道婆是崖州人。”羅燈光強調,“黃道婆居崖州37年,這是無論持哪一種觀點者都認可的事實。據此,我們要為黃道婆正名:她是崖州水南村原籍的村民,不是榮譽村民。”
黃道婆在崖州學藝30多年
向當地百姓學習紡織技藝
黃道婆的籍貫雖有爭議,但她在崖州學習紡織技藝,在紡織技術上作出巨大貢獻是不爭的事實。
羅燈光說,根據著名學者史樹青的說法,黃道婆生于1245年,卒于1306年。在崖州大約是15歲至52歲。“一個61歲的人,37年在崖州,崖州當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地區。”
1月5日上午,三亞日報歷史文化采風團驅車前往崖州,抵達傳聞為黃道婆曾居住的廣度寺(俗稱觀音閣)舊址,這里早已不見當年古寺的蹤影,建起了城西小學。林日舉攤開《黎族民間故事選》和自己的研究論文,帶領采風團成員穿越數百年歷史,回到黃道婆拜師學藝的古崖州。
《黎族民間故事選》寫道:黃道婆到崖州后,看見黎族婦女的棉紡織技術和工具都很先進,心靈手巧的她立志向黎族婦女學習,很快就掌握了黎族的紡織技術和工藝,織出了色彩鮮艷、有奇花異草、飛禽走獸等花紋圖案的筒裙、被面,令人賞心悅目,嘖嘖稱贊。
《三亞史》顯示,宋代,織吉貝布已成為黎漢同胞的重要生產活動。蘇東坡被貶儋州時就曾寫詩說一位黎族老人在寒冬贈他吉貝布:“遺我吉貝布,海風今歲寒。”宋元時期,紡織業在崖州具有一定的發展規模,崖州是海南南部紡織業和紡織品交易的中心。
“當時黎族紡織技術比較先進,而黃道婆在崖州生活了30多年,紡織技藝必定受到黎族先民的影響。”林日舉說,在《南村輟耕錄》里的記述也證實了這一觀點:“錯紗配色,綜線挈花,各有其法。以故織成被褥帶帨,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,粲然若寫。”所述的與黎族紡織業的工藝技術和圖案極為相近,因此,黃道婆在崖州向黎族人學習紡織技藝是成立的。
改造紡織生產工具
回鄉傳授紡織技術
在崖州30多年里,黃道婆從一個出逃女子逐漸長成了擁有一身織繡本領的婦人。然而“落葉”終要“歸根”。林日舉介紹,在元朝元貞間(1295年至1297年),黃道婆因思念家鄉告別崖州,“始遇海舶以歸”,返回松江烏泥涇。
“當時棉花種植已經在長江流域大大普及,但是紡織技術卻仍然很落后。”林日舉說。于是,擁有一身織繡好本領的黃道婆致力于改變家鄉落后的棉紡織業現狀,并結合自己幾十年豐富的紡織經驗,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精湛的織繡技術傳授給了故鄉人民。
黃道婆的貢獻主要可以分為兩點,一是改造工具,二是傳播“錯紗配色、綜線挈花”等先進的技藝。黃道婆在返回上海后,發現家鄉的紡車普遍使用的是舊式單錠手搖紡車,功效很低,很難滿足當時生產的需要。于是,黃道婆便找來木工師傅,經過多次實驗,終于將單錠手搖紡車改造成為三錠棉紡車,使紡紗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兩三倍,并在松江一帶很快得到推廣。
紡車效率提高了,但織繡技藝仍然比較落后,于是黃道婆借鑒我國傳統的絲織技術,汲取黎族人民織“崖州被”的長處,總結出了一套比較先進的織造技術,熱心向人們傳授。因此,當時烏泥涇出產的“被褥帶帨”等棉織物,上有“折枝團鳳棋局字樣”等各種美麗的圖案,鮮艷如畫。一時間,“烏泥涇被”不脛而走,引來上海、太倉等多地競相仿效,風靡全國。這些紡織品遠銷各地,很受歡迎,很快松江一帶就成為全國的棉織業中心,歷幾百年久而不衰。
18世紀乃至19世紀,松江布更遠銷歐美,被稱為“衣被天下”,獲得了很高聲譽。“可以說黃道婆就是黎族棉紡織技術的北傳使者。”林日舉說。
羅燈光認為,不管崖州是黃道婆的第一故鄉還是第二故鄉,三亞都要予以紀念。他建議建造黃道婆雕像,在城西小學立碑勒石銘記黃道婆遺跡,選擇一條路命名“道婆路”或者“織女路”等,讓黃道婆“重回崖州”。
三亞物華天寶,人杰地靈。古代的黃道婆解決了人們穿衣的問題,現代的袁隆平在三亞解決了吃飯的問題。羅燈光還呼吁將黃道婆與袁隆平結合打造成為“男耕女織”的“衣食父母”,這樣的創新宣傳模式將給三亞文化注入更多的活力,打造專屬三亞的文化旅游品牌。
(來源:三亞日報)
 推薦企業
推薦企業-
面向顧客,持續改進,實施品牌戰略,必須是
-
經編未來 無限可能
-
云展云舒,龍行天下 并人間品質,梳天下纖維
-
印染機械 首選黃石經緯 印花機 絲光機 蒸化機
 推薦企業
推薦企業
 推薦企業
推薦企業